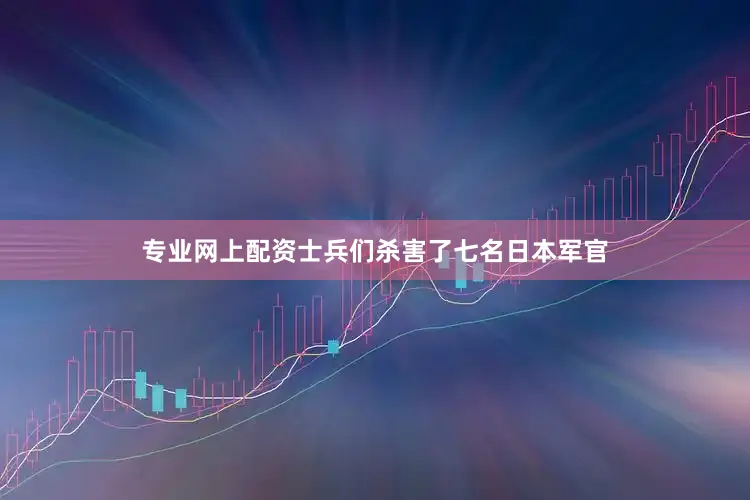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原因:列强争夺势力范围,民族矛盾激化。
1886年的长崎事件暴露了北洋海军纪律的松懈,而日本明治维新与清朝的洋务运动虽步调一致,但结果却大相径庭——前者勇往直前,开拓万里波涛,而后者则仅着眼于自我守成。在朝鲜壬午兵变中,24岁的袁世凯初露锋芒,而中日签订的《天津专条》则为甲午战争的爆发埋下了伏线。
在甲午战争爆发前的八年时光,北洋海军便已与日本展开了激烈的对抗。
1886年8月,北洋海军于朝鲜东海岸海域完成军事演习任务后,遂派遣定远、镇远、济远、威远等舰艇驶往日本长崎进行检修。此举标志着中国近代海军的首次日本之行,亦体现了清朝有意对日本施加的威慑。
清朝的洋务运动与日本的明治维新,几乎同步展开,两者亦不谋而合地致力于海军建设。一方是日薄西山的庞大清帝国,另一方则是蒸蒸日上的东亚新兴力量。在甲午战争爆发前夕,两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频生摩擦。正是在这场无硝烟的持久较量中,北洋海军以访问为名,抵达了长崎港。
两国间的紧张气氛早已在民间弥漫开来。8月13日的夜晚,北洋海军的士兵登陆寻求欢愉,却不幸与日本人发生冲突,进而引发了中国水兵与日本巡警、市民的混战,演变为一场大规模的械斗,导致多人伤亡。北洋海军的将士们群情激愤,甚至有人提出向日本开火的建议。
长崎事件事发后,中日双方迅速启动交涉机制,力求避免事态进一步恶化。李鸿章亲自会见了日本驻天津领事波多也章五郎,在两度交谈中,这位向来圆通的外交家采取了先严后宽的策略。他起初对日本巡警的无端阻挠清朝水兵表示强烈愤慨,指责其行为导致悲剧的发生;随后,他语气缓和,将事件比作儿童间的争执,并表达了对清朝与日本能够妥善解决争端的期待。翌年,双方达成协议,通过各自接受抚恤金的方式了结此事。
据说,在日清双方的冲突中,日本人趁机窃取了清军的密码簿。
风高浪急,危机将至。
在清朝激荡开展“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之际,日本亦在“黑船事件”的震撼中迈向明治维新。日本的倒幕势力凭借武力手段,成功颠覆了德川幕府的统治,进而创立了君主立宪的近代天皇制,随后迅速展开了近代化的改革措施。
与晚清洋务运动中倡导的自强与求富理念不同,明治维新明确地将改革目标细分为三大方针——富国强兵、殖产兴业以及文明开化。在这三者中,晚清洋务派的“自强”运动与日本明治维新的“富国强兵”均以军事建设为核心。

▲黑船来航:公元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驾驭四艘漆以乌黑的舰船抵达日本,凭借武力逼迫日本签署开放国门的条约。资料来源:网络
这两项运动表面上看似同胞兄弟,实则相差甚远。洋务运动始终恪守着一个核心理念,那就是——“中体西用”,其军事改革鲜有触及制度层面,而更侧重于技术革新,主要集中于武器装备的更新换代。相较之下,日本明治维新则提出了一套更为全面且深刻的军事改革方案。“和魂洋才”口号:保留日本民族精神例如,异化为军国主义武士道。持续吸收西方在政治、经济、思想、军事等领域的先进元素,对日本的技术、制度和政策进行深化改革。
无怪乎此,德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在觐见中国与日本的大使之后,直截了当地断言,此番中、日之间的较量,日本必将占据上风。俾斯麦之所以作出此判断,乃是基于这样一个观察:日本使节抵达欧洲后,纷纷投身于政治研讨与学术研究,渴望带回一身才干以推动国内变革。相较之下,中国使者中虽不乏具有远见卓识者,但大多数却处于混沌不明之中,对世界发展趋势茫然无知。
在日本军事领域,国家不仅引进了先进的武器装备,强化了军事教育体系,还进行了兵役制度的革新。此举取消了封建武士的特权地位,推行了全国范围内的国民义务兵役制,实现了军事征召的全国统一。同时,领导体制也迎来了变革,陆军省和海军省的设立,以及指挥条例的颁布,标志着军事管理体系的进一步完善。此外,编制体制也得到了改革,国家被划分为东京、大阪、镇西、东北等军区。在这些军区之下,设有步兵、骑兵、炮兵、工兵和辎重兵等多种兵种,构成了一个结构严谨的军事组织体系。(联队)为基本作战单位。
于晚清时期,由洋务运动催生的三大海军力量,在海军建设领域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福建、南洋、北洋)曾一度超越日本,北洋海军甚至被誉为亚洲之冠。然而,回顾那段历史,晚清的海军建设似乎自始至终都显得踌躇不前,缺乏魄力。
若将我国所有战舰直接部署,严密封锁敌方各海口,使其船只无法进出,这无疑是保卫我国海岸线的最佳策略。次之,则应采取守势……仅需守护关键数处,便能稳固防御。细细品味此段文字,不难发现李鸿章所强调的海军之用,在于“自守”,即在他国主动发起攻击时,我国得以凭借一支近代化的海军力量进行抵御,从而避免遭受打击。
相较之下,明治天皇在诏书中坦率地宣示,他们旨在“开疆拓土,威震四海”,其言辞间透露出明显的侵略意图。鉴于此,面对北洋海军建设的迟滞,日本民众迅速振作,全力以赴,在甲午战争爆发前成功打造了一支不逊于清朝的强大海军力量。
雄心勃勃的日本,在积极推进改革之际,亦同步培育了一种支持对外扩张的国内舆论氛围,将军国主义的思想潜移默化地融入了国民的认知与意识之中。
日本人崇尚明治维新思想家。福泽谕吉,尊称其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但福泽谕吉的另一个身份,是一名军国主义分子。福泽谕吉发表了《脱亚论》,提出了“脱亚入欧”的邪说,宣扬侵华主张,他认为,日本已经从亚洲的落后地位中脱颖而出,可以“移至西欧文明”,像西方列强一样侵略、瓜分东亚邻国,“对待‘支 那’、朝鲜之办法,不必因其为邻国而稍有顾虑,只能按西洋人对待此类国家之办法对待之”。
踏上强国征途的日本,却终究误入歧途,走上了军事侵略的道路,其锋芒直指周边邻邦。朝鲜“征韩论”声势浩大,弥漫于世。中日之间的战争,即将在朝鲜半岛拉开序幕。

▲福泽谕吉。图:网
朝鲜,在中华宗藩体系的庇护下,长久以来默默承受着庇护国的恩泽。然而,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它显得无所适从。毕竟,连作为“家长”的清朝都屡遭挫折,留给朝鲜的余地愈发狭小。法国、美国等西方列强,凭借坚船利炮,步步紧逼,要求朝鲜敞开国门。清朝的总理衙门自知无力捍卫朝鲜,只得劝其与西方国家建立联系。弱国无外交,此言不虚。
1876年,崭露头角的日本意图分得一杯羹,遂派遣一支海军远赴朝鲜,迫使朝鲜签订了一份不平等条约。《江华条约》本条约中,日本“承认”朝鲜为独立国家,赋予其与日本同等权利,并要求双方互派使节。朝鲜须开放通商口岸,日本公民在这些口岸享有领事裁判权。这几项条款,清朝自是耳熟能详。尽管这些是日朝间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然而其本质无疑是对清朝的公然挑衅,揭示了清朝作为宗主国的名不副实。随后的数年间,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家亦与朝鲜签订了类似条约,纷纷瓜分朝鲜的利益。
在列强的掠夺式侵略面前,朝鲜国内局势动荡不安。
年轻的朝鲜国王李熙(亦即朝鲜高宗,1864年至1907年间执掌朝政),即位后一度依靠“大院君”李昰应巩固政权。所谓的“大院君”,乃朝鲜一高爵显位,权势显赫。李昰应曾三度执掌朝鲜国政,在朝鲜近代史上屡次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故而众多史籍便以其尊号“大院君”称之。此外,大院君李昰应还是朝鲜国王李熙的父亲,父子二人均出身王室旁系,恰逢朝鲜外戚安东金氏势力倾覆,时局动荡,二人便因缘际会走上政治舞台。儿子继位为君,而父亲则辅佐朝政。
李熙的王妃闵兹映出自朝鲜显赫世家,她亦是一位颇具政治谋略的女性。鉴于日本与朝鲜签订协定,她力主引进日本的影响力,并聘请了一批日本军官来朝鲜对军队进行训练。闵妃表面上以借助日本之力推进改革为名,实则是在暗中培植心腹,以抗衡大院君的势力。
李熙置身于生父与宠妃之间,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仿佛身处人间的夹缝之中。这场宫廷的权力争夺战,最终演变为中日之间朝堂纷争的导火线。

▲朝鲜李熙国王。来源:网络。
1882年,大院君李昰应着手对付闵妃及其背后的朝鲜亲日势力。(即所谓“开化党”),发动了“壬午兵变”如前所述,闵妃采纳了日本人的建议进行军事改革,这一举措迫使众多原本的朝鲜军人失业。大院君趁机煽动军士士气,鼓动那些未能领到军饷的朝鲜士兵起义,意图对抗亲日派。在起义中,士兵们杀害了七名日本军官,并将日本使馆付之一炬。此举使得日本公使惊慌失措,急忙逃回本国。同时,闵妃集团中的众多官员亦在此次起义中丧命,而闵妃则伪装成宫女,侥幸逃离皇宫,侥幸逃过一劫。
大院君意图通过兵变掌握政权,却未曾察觉到朝鲜上空那双无形的巨手。中国,作为朝鲜的“长兄”,始终密切地关注着朝鲜的任何动向。而日本,觊觎着“长兄”的地位,亦怀有在朝鲜攫取更多利益的野心。
一旦“壬午兵变”爆发,中日两国便迅速对朝鲜采取了军事行动。
大院君未能如愿坐稳摄政之位,却意外地引来了外患,更使得一位中国青年得以踏上晋升的阶梯,那便是年仅二十四岁的他。袁世凯。
袁世凯青年时期便深陷科举制的残酷打压,虽在河南屡次尝试乡试,却屡遭挫败,终未能金榜题名。
对于这位出身于官宦世家的青年而言,这无疑是一场巨大的打击。
袁世凯一脉,堪称晚清时期崭露头角的汉人显赫官宦家族。
袁世凯的叔祖袁甲三昔日,袁甲三与曾国藩、李鸿章同列朝堂,并肩作战,共赴战场,助力平定了太平军与捻军的叛乱。当李鸿章在淮南指挥军队时,袁甲三则驻守淮北,二人情谊深厚,相互敬重。李鸿章曾以书信致意,尊称袁甲三为“年伯大人”,对其指挥才能赞誉有加,认为他领兵作战游刃有余,屡次攻克坚城,被誉为“福星”。袁甲三离世之后,其麾下众多士兵被编入淮军,袁、李两家的关系也因此更加紧密。及至第二代,袁世凯的叔父袁保恒、袁保龄以及嗣父袁保庆等人,要么曾是李鸿章的得力助手,要么在洋务运动中出谋划策,均得到了李鸿章的力荐。
“男儿应以驰骋沙场为己任,捍卫国家,抵御外敌,岂能长期沉溺于文墨之中,浪费宝贵时光?”
1881年,袁世凯毅然放下手中的笔,投身军旅,加入了驻扎于山东登州的淮军将领麾下。吴长庆“候选中书科中书袁世凯,治军严谨,善于剿抚,建议在省分同知分发前先予以补用,并赏赐花翎以示嘉奖。”此后,袁世凯随吴长庆一同驻守朝鲜首都汉城。(今韩国首尔)。
袁世凯由此成名。

▲袁世凯。图源:网络
仅过33日,大院君便在兵变的风波中落网,被清军拘捕,送往中国软禁。清廷之所以迅速派遣军队入朝平定乱局,旨在重申中国在朝鲜的势力范围,抵御日本的政治渗透。然而,日本人的洞察力依旧敏锐,他们以朝鲜境内日本人遇害为由,迫使朝鲜签订《仁川条约》(即《济物浦条约》),不仅成功索得赔款,更借鉴中国经验,获得了向朝鲜派遣军队的权力。
壬午之变后,中日两国均在朝鲜半岛扶持了自己的代理人。一方被称为“事大党”,其主张事大主义,顾名思义,即继续效忠宗主国清朝,与我国关系亲近;另一方则为金玉均以等人为首的“开化派”,积极倡导借鉴日本模式,尊奉日本为师,力求实现国家的近代化转型。
中法战争(点击阅读)一经爆发,清朝便陷入了与法国的激烈冲突,无暇他顾朝鲜的局势。1884年12月,在时任日本驻朝公使竹添进一郎的煽动下,“开化党”领袖金玉均策划并实施了。“甲申政变”暗中图谋刺杀“事大党”的官员,进而引诱日军攻入王宫,并胁迫国王李熙就范。金玉均意图在朝鲜复制一场“维新”,公开宣布解除中朝间的宗藩关系,却未料自己不过是沦为日本的棋子。
闻悉朝鲜政变的消息后,清军迅速作出反应。驻留朝鲜的袁世凯再次展现了出色的能力,他迅速致信远在旅顺的四叔袁保龄,提出了四项稳定朝鲜局势的策略:首先,力保朝鲜的安全,因为朝鲜是至关重要的屏障,若其落入日本手中,将严重损害整体局势,其后果不堪设想;其次,避免与日本开战,鉴于中法战争尚未画上句号,清朝不宜同时与多国交战;第三,请求派遣兵力支援,建议派遣高级将领入驻朝鲜,以掌控全局;最后,释放大院君回国,以此削弱朝鲜亲日派的影响力。袁保龄在接到袁世凯的信件后,立即将这些建议转达给李鸿章,为清政府后来处理“甲申政变”提供了宝贵的参考。
在朝鲜半岛,年仅26岁的袁世凯便显露出了其果断杀伐的锋芒。在向袁保龄发出信函后,即便尚未接到清廷的具体指令,他亦迅速着手行动。
吴长庆已移驻金州。(今辽宁金州)同年,袁世凯执掌汉城驻军,他首先致函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声称应朝鲜国王之请,将率军入宫,以护卫国王安全,绝无他意,并恳请日方给予充分配合。此次政变显然是日本人暗中操控,竹添进一郎心知肚明理亏,却拒绝回应。然而,袁世凯假装不知竹添进一郎的阴谋,故意高调支持朝鲜,从而在外交上赢得了先机。
随后,袁世凯迅速率领军队入宫,于混乱之中成功救出朝鲜国王李熙。李熙抵达袁世凯的军营后,确认自身安全,随即公开发声,严厉指责“开化党”成员金玉均等人犯上作乱、戕害大臣,并强烈要求日本方面不得偏袒叛乱势力。鉴于国王已得解救,叛乱势力丧失了关键筹码,不久便如鸟兽散去。政变发生后第六日,即12月10日,袁世凯亲自护送李熙返回王宫,随后他亦率兵驻扎宫中,严密布置以防生变。亲日的金玉均未能得手,最终逃往海外,十年后在上海遭到另一位朝鲜人的刺杀。
在袁世凯的不懈努力下,清朝依旧牢牢把握着对朝鲜局势的操控权。日本人不禁感叹:袁外交,手段强悍。
然而,日本不愿徒劳无功,遂将责任推卸给日本公使,紧接着便与清朝展开了交涉。1885年3月,由伊藤博文担任全权大使、西乡从道担任副使的日本代表团抵达天津,就朝鲜问题与中国进行商谈。清政府则派遣了以李鸿章为首的“签约专家”作为代表参与谈判。
伊藤博文坦率地陈述了日本方面的诉求,这包括对驻朝清军将领的惩处、对遇害日本侨民的赔偿,以及两国携手从朝鲜撤军的建议。
清朝不愿同时陷入中法、中日战争的泥潭,最初曾倾向于向日本妥协。所幸,中法战争前线镇南关大捷的捷报传来,使得清朝代表得以振奋精神,态度稍显强硬,未完全满足日本的无理要求。最终,中日双方各让一步,成功避免了局势的进一步恶化。1885年4月18日,中日双方正式签署了相关协议。《天津会议专条》,其中有一条规定,一旦朝鲜遭遇重大动荡,双方均可动用军队,同时必须相互通知。甲午战争伏笔已种。
甲申政变得以平定之后,其结果与同一时期发生的镇南关大捷在某种程度上展现出异曲同工之妙。在这两场关键的较量中,清朝均成功夺取了军事上的胜利果实,然而在随后的谈判过程中,却显露出了软弱无力的态势,导致主动权的丧失。

▲李鸿章。图源:网络
国家多舛,然而对袁世凯而言,他却成就了一桩伟业,深得李鸿章的青睐。1885年3月,袁世凯归国述职,得以拜见李鸿章。在二人就朝鲜局势的深入探讨中,李鸿章对袁世凯进行了即兴“面试”,对其表现十分满意,并对其才华给予了高度评价。不久之后,袁世凯计划返回河南故里探望亲人,并向李鸿章表达了自己欲卸甲归田、专心奉养双亲的愿望。然而,李鸿章却告知他,一个月后需北上京城,朝廷有重要任务交由他负责。
清朝委派官员。“朝鲜总理商谈通商”袁世凯凭借屡次建树功勋,成功赢得了官职的青睐。在1885年至甲午战争爆发前的十年间,他担任了清朝在朝鲜的全权大使,其地位可比肩“监国”。至此,他在晚清政治舞台上确立了坚实的地位,占据了不可忽视的一席之地。
日本意图借助“开化党”之力掌控朝鲜,却遭袁世凯搅局,尽管如此,他们仍对朝鲜这块肥沃之地虎视眈眈。
清朝派袁世凯驻朝,旨在巩固边疆。“阐明尊亲之道,坚定动摇之志,内务政治修明,外交邦交和睦。”此举措旨在维系清朝与朝鲜间的宗藩纽带,同时阻止日本、俄国等势力对朝鲜的进一步渗透。
日本在外交领域屡屡碰壁,无奈之下,只得再度借助朝鲜的内部动荡,制造事端。
1894年,一场足以改写中、日、朝三国历史进程的动乱,正悄然逼近,一触即发。
与中国和日本相似,朝鲜在国门敞开之际,同样沐浴了西学东渐的洗礼。然而,这突如其来的变革既让某些人得以摆脱愚昧的束缚,却也引发了另一部分人的惶恐不安。
东学道,这一由不得志的朝鲜书生崔济愚所创立的教派,其宗旨旨在抵御以天主教为代表的西方学术。所谓东学,即东方学问的简称。崔济愚对中华文化圈中的儒家、佛家、道家三教深怀仰慕,从中汲取教义精髓,倡导民众抵制外来学问与外籍人士。该教派的信徒以农民为主,广泛分布于朝鲜南部的庆尚、全罗二道。
历经数载的弘扬教义,东学道信徒的人数迅猛增长,逐渐演变成一股不可小觑的政治力量——东学党。
东学党人频繁进行公开活动,甚至联名上书国王,恳请驱逐外国人。袁世凯深觉这些人终将引发祸端,遂向李鸿章发出电报,言道:“东学邪教,联名上书韩王,力主驱逐洋人。接连散布揭帖榜文,沿街巷口对西方人士进行诟骂,声称将进行驱逐与杀戮。此举使得汉人和洋人都深感恐慌。日本人纷纷携带刀剑在白天行走,整个局势愈发动荡不安。”
“琼浆玉液,千杯尽染英雄血;珍馐美味,万口同尝黎民脂。烛光摇曳,泪滴成行,百姓亦随落泪;歌声绕梁,怨声四起,悲鸣响彻云霄。”
1894年初,全罗道古阜郡(韩国全北道井邑市)的东学党领袖全琫准深受信众与农民的爱戴,他们发起起义,高呼“驱逐倭寇,净化圣道”、“剿灭权贵,恢复国家安宁”的口号。东学党人在占领郡衙后,敞开仓库,分发粮食和钱财,因而赢得了广泛的民意支持,迅速蔓延至半岛各地,掌握了朝鲜南部三道的控制权。

▲东学党起义遭受挫败,全琫准随之被捕。资料来源:网络
在应对迅猛发展的叛乱浪潮之际,部分朝鲜官员提议向“大哥”寻求支援,意图借助清朝兵力进行镇压。朝鲜大臣闵泳骏与袁世凯频繁会面,商讨借兵事宜。袁世凯毫不犹豫地应允:“朝鲜若遇危难,我岂能坐视不救?一旦遇到难题,我定当全力承担。”
“袁世凯必有其应对之策,陛下无需为此忧虑。”于是,李熙坚定了借兵的决心,正式向清朝伸出了援手。尽管清朝不愿放弃宗主国的尊位,最终还是同意派遣军队支援朝鲜。
实际上,朝鲜未能察觉到日本的勃勃野心,且过分估计了清军的战斗力。早在1885年的《天津会议专条》中便已载明,一旦中国向朝鲜派遣军队,日本便以此为借口介入。日本在清朝身上埋下的隐患,此刻已显露无疑。
1894年六月,清政府向驻日公使汪凤藻发出电报,向日本政府通报,我国政府应朝鲜之请,依照“我朝保护属邦旧例”,决定派遣军队增援朝鲜。
日本对此作出了回应,首先强调,日本从未承认朝鲜为中国的附属国。其次,依据《天津会议专条》的规定,鉴于朝鲜目前正遭遇重大动荡,日本以保护侨民及使馆安全为由,计划派遣军队赴朝鲜执行任务。
清军分作三批次渡海赴朝鲜,协助该国平息东学党起义之乱。与此同时,日军亦大规模进兵朝鲜。至6月16日,日军在仁川成功登陆,其入朝的混合旅团兵力已逼近四千人。显而易见,日军的真实意图并非仅仅针对东学党,其野心远在朝鲜全境。
自那以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中日两国展开了新一轮的交涉。在清朝的权力核心中,意见出现了分歧,一方主张战斗,另一方则倾向于和平。最终,朝廷决定采取双管齐下的策略,既寻求通过谈判促使双方撤军,又准备派遣军队,期望能在谈判桌上说服双方避免冲突。然而,日本政府早已蓄势待发,意图与清朝一决高下。他们发出了所谓的“第一次绝交书”,态度强硬地宣称:“若与贵政府意见相左,我国断然不会撤回目前在朝鲜的驻军。”
清政府虽自身力不从心,却寄望于外国援助,试图借助英、俄等国之力进行斡旋,“起初借助俄国人以施加压力,继而依赖英人进行调停”,然而列强却乐见中国内部争斗,清朝的如意算盘最终落空。
清政府的犹豫不决,为日本部署军队赢得了宝贵的时间窗口。
日军的铁蹄踏入朝鲜,袁世凯在朝鲜多年的基业遭遇了空前的危机。当日军抵达汉城,将一门门大炮瞄准了他的官邸,中日之战一触即发,袁世凯仿佛成了炮火下的靶子。关键时刻,英国驻朝公使朱尔典挺身而出,巧妙地让袁世凯得以藏身于英国使馆。夜幕低垂,袁世凯在朱尔典的协助下,化装成普通人,悄然离开了那座危机四伏的官邸。
1894年7月,正当丰岛海战的风云际会即将来临之际,袁世凯已从仁川港登舟返回祖国,从而画上了他在朝鲜驻留十年之久的句点。而他的离去,预示着一场惨烈的战役即将在朝鲜半岛上拉开序幕。
倍享策略-炒股怎么加杠杆-正规的配资公司有哪些-专业杠杆配资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